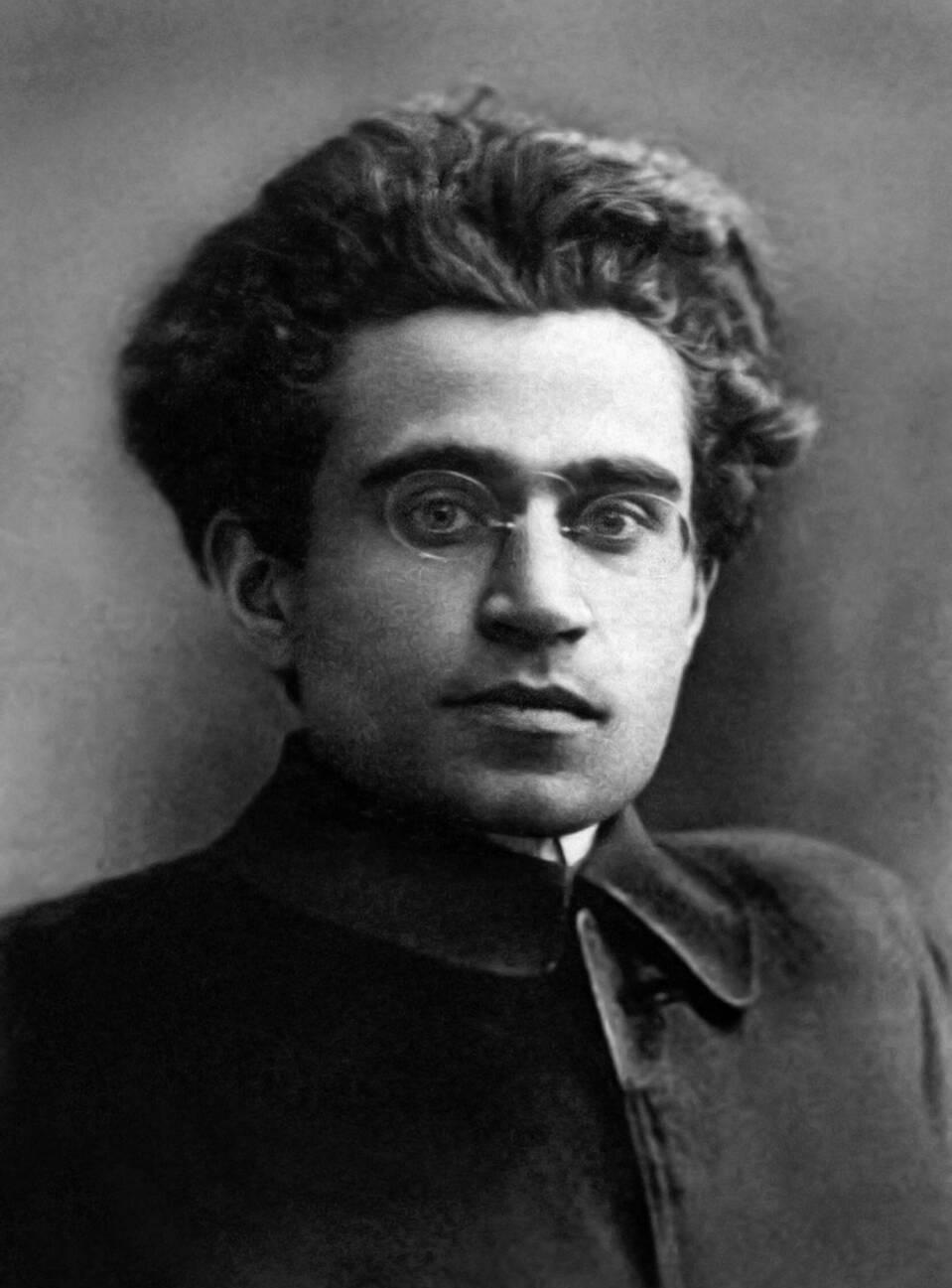国产精华液一线二线三线:李宗瑞吴亚馨-孟泽:我们简化了历史,因此也简化了人性
近年来读书,不再为自己在大学里所从事的“专业”所左右,更加“随心所欲”“兴之所至”了。这既是自己读书原本从来不讲规矩的“性质”使然,也是想要接触的人物和求解的历史让我不能不“移情别恋”,移情别恋的最大端,就是湖湘人物留下的文字。
晚清湖湘,因为特殊的文化水土,特殊的历史机缘,一时人文炳蔚,英雄崛起,其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更是出类拔萃,光彩照人,戏仿梁启超的口吻说,他们不止是晚清不一二睹的大人物,更是中国历史上不一二睹的大人物。
他们巨大的“事功”、强悍的意志和丰沛的情感世界,首先自然得益于他们本人不平凡的禀赋,同时与那个特殊时代所产生的的史无前例的历史需要有关,而在精神深处,则联系着他们所遵循的思想和禀承的教养。
尽管从某种我们熟悉的历史观看,他们的“事功”并不具有充分的政治正确性,他们的努力所对应的是一个充满原罪的不堪救药的衰朽王朝,这个王朝的覆灭,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如此,他们对于这个王朝的拯救,不免显得无谓和可疑,甚至显得荒谬和反动。他们一度显赫的“事功”,将无法不黯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忽略,被遗忘,或许还要被敌视和诅咒。此所谓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常常不过一纸之隔、一纸两面而已。我们无须纠结于此。
真正让我们动心并且用心究诘的是,历史的逻辑,并不遮蔽和否定历史主体的光辉,个体生命的自主自胜与强力意志,人的尊严与意义,历史转折处风云际会者的悲剧精神及其英雄气象,其拯救与自我拯救,其解放与自我解放,常常有着独立于具体历史正义的属于人和人类全体的普遍正义和崇高,这种正义和崇高,同样暗示出主体在自我确立过程中的魅力,暗示出人性人道的某种永恒属性。
他们所奔赴的天命,自然是基于“家”“国”一体、“政”“教”合一的“君父”之命,让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敌人,则同样是啼饥号寒而被他所服膺的“主义”命名为“盗匪”、被他广大的悲悯所排除的苍生。但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投身献身,那种全力以赴的自我成全,却终究也是任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存在所试图寻找的托身之所和止归之处,吊诡的历史常常盛开着让人难以草草辨识、难以简单分别、难以轻松取舍的“恶之花”。
其时,从朝廷到地方,无论“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同样地被那些无休止地上演的虚荣伪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所败坏了”,整个国家,因为体制上无解的因循与结构上不能真正自我更新的封闭,因为极权的垄断性与自身不可抑制地生长的腐蚀性、破坏性,也因为肉食者的贪婪、懒惰、残暴、麻木、玩世不恭、良知泯灭而一天天堕落衰弊下去,上下相蒙,官民隔绝,统治集团演变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而天聋地哑、无由上达的底层社会,则只剩下哀哀待毙的贫穷、绝望和悲苦,他们中间少数富有生命力的人,不免要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以性命搏出路,最终葬身于骨山血海。
同治二年(1863年)《复毛寄云》信,左宗棠言及浙江战后的现状时说:“惟灾黎满目,田野荒芜,无以为计。纵岁事大稔,吾浙犹多不登食籍之民,殊可悲也。现因淫雨弥月,仅存之豆、麦、春花亦复无望。衢、严各属与杭、湖傍山各县,竟有人相食者。虽各设粥厂并运谷米,收买铜铁、铅锡、茶叶,聊纾旦夕之死,而杯水车薪,于事鲜济,真不图天地间竟有此等变相地狱也。”几乎同时在《致曾国荃》信中,左宗棠说:“入浙以来,日见凋耗情形,心酸泪落,即杭城而论,昔时户口八十余万,今之存者,不过四五万而止,而又或鳏或寡或孤或独,无一家骨肉得完者,哀我人斯,竟至于此。”
如此这般的现实,所激发出来的良心血性,很难不让人产生以身许之的期望,产生拯饥救溺的冲动。曾国藩们的作为,正是可以范围在这种期望与冲动之中。他们出身有别,禀赋参差,但教养相仿佛,德性人格有着相似的谱系和调性,都是传统文化陶冶出来的宁馨儿:履历非常,性情丰赡、精神饱满、人格光昌。他们留下的文字,照见幽暗的历史,也照见幽微的人心,洞彻天地,贯通古今,读起来常常惊心动魄。
中国文化是一种弱宗教性的文化,为人处世的智慧,往往体现为一种教养,而不是一种戒律,个人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出于自觉而不是强制,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读到一种基于自我建构的有关家国天下的建构,关于自我的规训与安排,他们的道德文章与功业,是从严格的修身——自我规训开始的,并且常常以这种自我规训作为训育子弟、维系家国、立功天下的起点和终点,所有谋国、淑世、立人的哲学,无不基于“反求诸己”的修身自律,基于成人成己的抱负。
咸丰十一年,左宗棠(1812-1885年)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生尔等最迟,盼尔等最切。前因尔等不知好学,故尝以科名歆动尔,其实尔等能向学作好人,我岂望尔等科名哉!
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聪明强固,盖义理悦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诵读而无得于心,如和尚念经一般,不但毫无意趣,且久坐伤血,久读伤气,于身体有损。徒然揣摩时尚腔调而不求之于理,如戏子演戏一般,上台是忠臣孝子,下台仍一贱汉。且描摹刻画,勾心斗角,徒耗心神,尤于身体有损。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
引用这一篇有点冗长的文字,试图发现的是左宗棠对于他所处世界的认知和作为士大夫的自我认同,这种认知和认同以及由此出发的对于人、人才的定义与斟酌,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性,一个人道的世界正是从无量数的历史人物的淬炼中延伸过来的。左宗棠出身寒素,但毕生勇猛精进,处世行事,大气蓬勃,同时心思缜密,手眼周详。他做人有道,教子有方,谋勇兼胜,很多方面都可以是励志的榜样,他对于家国天下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令人亢奋激动。
一般来说,一个与所处时代有着深刻而广大的互动纠缠的大人物,其气质性情与人格,往往都充满着令人惊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如约翰•罗斯在《拿破仑一世传》的开篇所说的拿破仑:“他的性格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结合——刚强与文雅的结合,激情与理智的结合,北方人的求实精神与东方人的丰富想象的结合。而这些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特点在他身上的结合,可以说明他一生中的许多神秘事迹。对于传奇故事的爱好者说来,幸而天才的人物是不可能完全分析清楚的,无论是最敏锐的历史哲学家,还是最认真的遗传学大师,都无法做到这点。”这段关于拿破仑的分析,用在左宗棠身上,也并不显得夸张突兀。他是狷介的,又是通达容忍的;他是旁若无人、发扬蹈厉的,又是洞悉机要、体贴入微的;他是进取的,又曾怀退隐之志,要长作击壤之民;他无事不欢,大包大揽,又见微知著,冷静专一;他是自负的,然而也是自卑的;他铁腕行事,雷霆霹雳,却自有低眉俯首的时候,连他的温情和哀伤,也常常带有强悍强势的味道……
一个时代的英雄,常常预示着一个时代可能的走向。
左宗棠豪气干云的事业心与功名心,他的缺少反思性的天才自负和舍我其谁的硬汉气魄,他对传统体制及其文化的无所保留的服膺,在一个面临“三千未有之大变局”的仓皇时代,阻碍了他对于现实有更具前瞻性的把握。他自以为是的也被世人广泛称道的不世事功,大多只能在传统价值体系之内才能获得肯定。在他身上,真正可以让他所面对的世道起死回生的近代意识十分淡薄,他对西方的认知,范围在他自胜胜人的主观意志之下,按照他的方式所从事、所主导的“洋务”与“自强”,从起点上就并不符合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对于日薄西山的时局和世运,只有补苴罅漏的功能而少有贞下起元的意义。
这正是左宗棠作为晚清“英雄”的致命局限。他与近代世界的隔膜,代表着晚清精英群体的普遍隔膜,由此而来的是面对新世界的无知、傲慢、颟顸与措置失当,以至肇端了差不多二百年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挫折和悲剧,因为挫折与悲剧,让我们对于原本应该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历史,不能不充满焦虑和怨恨,由此我们甚至不愿意太多了解和欣赏他们作为历史当事者、作为不世出的人物的精采与蓬勃。
然而,历史从来不只是关于过去的故事,历史人物也不只是某一种制度和文化的穿线木偶,最滥污的历史中也会有耀眼的人性的与神性的光辉,而那种让人惊艳的人性与神性,甚至就是我们存在的家园,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记忆,是我们唯一可以皈依的故乡,所谓人道正是记忆的苏醒,是故乡的召唤,残损的性灵由此获得滋养,短缺的现实由此得到补救。
已经不止一个世纪,我们的生活一直伴随着宏大的题旨和崇高的使命,一些万众一心的目标和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垄断着我们,让我们颠颠倒倒,欲仙欲死,我们试图中断僵固的历史,抹去不堪的记忆,我们期待可以推倒重来,以期获得完全的新生,结果却常常只得到肉体的轮回——一代一代人的牺牲,无关乎灵魂的超拔。我们总是兴冲冲地出发,又一败涂地返回,辛酸的痛苦的旅程,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前车之鉴的经验和智慧,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至今折腾在自以为是的远大前程中,很少看懂深渊一样的自我,看清眼前和足下的虚实。我们牵挂全世界,但很少反思自己,我们关心别人的罪,很少关心自己的孽,我们害怕空虚,讨厌孤独,向往广场,崇拜潮流,一不小心便迷失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初衷,遗忘了自我的立场和标准,舍弃了人之为人的来源与去处,并以此不着边际地自豪和骄傲。
这一切当然不是单一元素带来的因果,但无疑与我们简化了历史因此也简化了人性有关,与我们失去了记忆也因此失去了家园有关,与我们没有接纳从数千年文明延伸过来的人的基本定义与章程有关。
如何真实地拥有自己从肉到灵的生活?如何明心见性,洞彻从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涌起的黑暗和光明?历史悠远,现实寥廓,世事苍茫,我们需要从出发的地方寻找初衷、动机和可能性,需要从树根长出的地方重新寻找阳光和空间,而这正是“君自故乡来”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本为《君自故乡来》自序;《君自故乡来》,团结出版社2025年4月版)